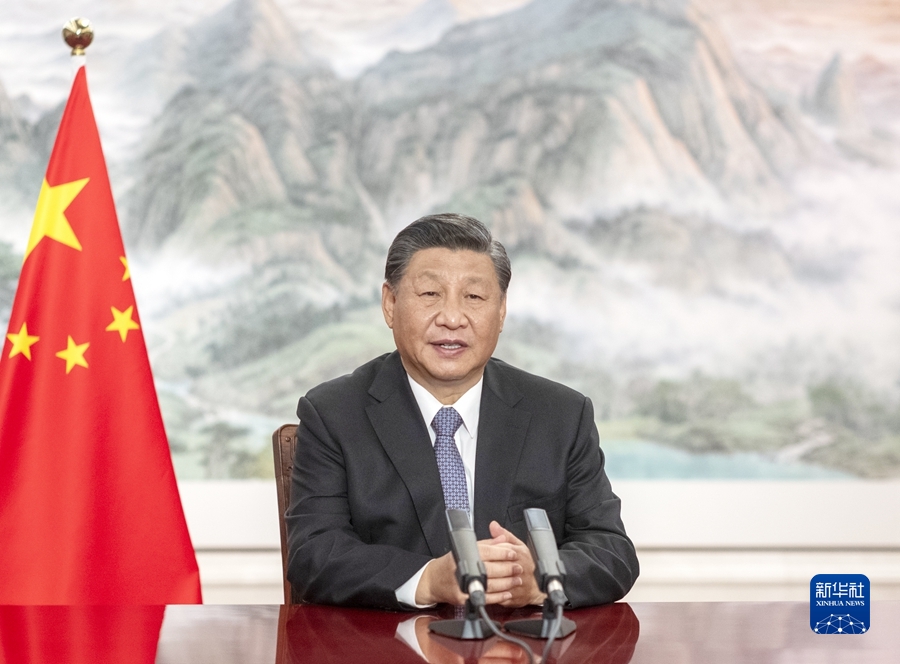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天津美术学院副教授、理论批评家范晓楠博士与参展艺术家——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雕塑青年创作中心雕塑家、中国雕塑学会会员景晓雷,就近年来的创作进行了深入对谈。

策展人范晓楠(左)与雕塑家景晓雷在后者本次参展作品前合影。
范晓楠:持续半年多的新冠疫情造成世界范围内的灾难令人震惊,这似乎预示了人类未来所面对的巨大威胁。你将自己的作品定义为面向未来的创作,与科技以及人类未来的生存处境密切相关,并抱有担忧的乐观态度。面对今天的疫情,你依然乐观吗?对于今后自己的创作又有怎样的思考?
景晓雷:纵观人类历史,生存是首要问题。战乱、饥荒以及瘟疫占据了大部分历史。只有近几十年的时间我们才处于相对和平的时期。核武器的出现使各大国互相牵制而未发生大规模战争。抗生素的出现也使我们能够对细菌进行有效控制。受人类生命周期的局限,我们只能感受到近百年的时间。这就使得大多数当下人误以为世界本该就是和平与繁荣的。
对于一个生物群体而言,疫情只是类似历史中的一个点,比如14世纪黑死病肆虐欧洲,虽然夺去2500多万人生命,但对人类来说不足以构成毁灭性打击。当然对于个体来说是百分之百的灾难。也有人认为人类当下做的种种事情,比如各大国手中的核武器、基因编辑工程、人工智能等,无异于自掘坟墓。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争端问题,而一个家庭内部再大的问题,比如兄弟反目,最终家族也并不会因此消失,只是换了形式而已。真正使他们受到毁灭性打击的力量来自外部。地球也是如此。
我今后的创作主要延续两个方向。
一,对于空间的探索。我们身处的宇宙是由量子构成的,每个量子存在多种不同状态,那么我们推论宇宙也或不止一个,这就出现了平行宇宙的理论。我试图通过物理方式感知另外空间的存在。但工作方式与科学家不同,我利用当下手段并通过有计划地实施将它“呈现”。对于这方面的兴趣也许源于学雕塑过程中对空间探索的兴趣吧。
二,我对所有新鲜事物都保有好奇与激动。从技术进步到当下人工智能雏形的出现,甚至生物基因学上的发展,我对这些未知领域都有极大的了解欲望。这些领域的发展受制于人文主义的框架,再加上人性特点等因素,未来呈现的人类社会的结构会是什么样?我对此充满兴趣。
范晓楠:纵观美术史的重要变革时期均与科技革命的时代背景相伴相生。现代艺术伴随第二次科技革命出现,当代艺术在二战后伴随第三次科技革命诞生。进入2020年,专家们预计人类将迎来第四次科技革命: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机器人技术、生物技术、量子计算技术,纳米技术、互联网、无人驾驶技术等,那么未来的艺术又将呈现怎样的发展态势?
景晓雷:从技术角度来看,近百年是人类突飞猛进的时代,技术刺激着当下每一个人,包括艺术家。艺术家利用技术打开思维或者说开启另一双眼睛。而技术发展是有瓶颈的。首先,早有学者指出摩尔定律其实十年前就已经失效了,在计算机领域我们不可能像以往那样每18个月计算速度就翻倍,这就说明制约计算速度的不只是技术而更是基础物理认识。基础学科的突破会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从观念的本体来看,从杜尚将小便池放入美术馆的那一刻起,当代艺术就已经定型了。这一百年中我们一直笼罩在他的阴影之下,难以突破。几万年的过程中,人类大脑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在同样的环境之下思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这就说明未来如果要出现伟大的艺术必须是先有时代突变。这里面需要一些因素的出现,比如大到影响地球大多数人的变革或战争,比如基础物理学的突破改变我们的认识。
未来的艺术在短时期内,技术的应用会比以往更加多样化,艺术家创作更偏向于理性,但要有突破性进展,需要多种因素的长期合力。
范晓楠:在你的作品中,你希望呈现仿生技术与人工智能的结合,从你近期《世·界》的作品,对雕塑、激光以及烟雾等媒介营造沉浸剧场的尝试,已经打破了你以往不锈钢单体雕塑的呈现。《世·界》首展在武汉合美术馆大获成功,这次在悦美术馆根据展陈空间,你又重新设计作品的布展方案,可以结合新的方案谈谈你的创作角度以及作品最终的展示效果吗?
景晓雷:从2008年起,我尝试着做和未来人相关的一系列作品,当初只是从社会科技的发展思考人的变化与提高过程。这里需要说的是,人这个物种几万年没什么变化,当相关新技术出现时必然会通过外力来突破自身的进化瓶颈。当下我们能够看到人类自我提升的方式有三种:一是仿生技术,二是基因技术,三是人工智能,而这三种方式中当下发展最好的就是人工智能,而另外两个由于人文主义的影响,社会不可能大张旗鼓地放开来研究。尤其是基因技术,这就促使我把思考的重心从技术与形态逐渐转向到未来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上。单一的雕塑的方式就很难满足这一点。

景晓雷作品:《世•界》
从《世·界》这组创作开始,我将雕塑变成了我完成作品的材料,所以它并不是做完就结束的作品,而是后面一个个作品的开始。这就需要思考展览的场地和周围的环境。在合美术馆面对的是个独立空间,有条件将环境作为一个暗室呈现,我可以将环境最大范围考虑进去,作品甚至延伸至每一个角落。我将它看作是一个小型的宇宙空间,探索平行宇宙的关系,并且尽我所能地用物理方式,打破美术馆方盒子的概念,使人们能够亲身感受到另外空间的存在。而悦美术馆是一个开放的“白空间”,在展览过程中每件作品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我通过三件作品相互关联,恰好可以表现我对未来社会构架的思考。
范晓楠:你很喜欢不锈钢这种材质,并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在创作和制作中,每件作品都需要持续几年时间,强调作品的工业感和去人工的痕迹。经过多年实验和创作后,你对自己以往的作品有怎样的评价,自己认为那些作品比较成功?哪些落地的项目与空间环境的关系更符合自己的预期?不锈钢的材料本身是否也有它的局限性,未来希望更多地尝试探索与新媒介的结合吗?
景晓雷:在我最早的作品《圣祭》的完成过程中,每一片金属都是我自己磨砺出来的,这个过程很煎熬,使我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人的渺小,你必须虔诚地用大量时间与精力去完成。而作品的加工如同绘画的语言,它是思想的反映。去掉所有的人工痕迹,这也恰恰是我对未来世界的认识体现。
我的作品从最初的《0度空间》系列开始,《骨》系列,再到《风物》系列,以至于今天的作品《世·界》,这是个线性的过程。在我的创作中,我从来没有想过做完一个系列再做另外的系列,它是一个综合体,是我对未来整体的看法,不能分割也不会结束。

景晓雷作品:《地脊》
谈到公共落地项目的话,2014年落成青岛世园会作品《地脊》,全长28米,从大地穿出一根脊梁再落回大地,这是我用自己的作品风格第一次尝试公共艺术。
2018年,作品《预言》落地在腾格里沙漠,这使得一直困扰我的如何将时间因素带入到作品中的问题得以解决。沙漠是个神奇的场域,像一个自然规则忠诚的守望者,没有人类社会的痕迹,一种回归到本原的静止。走在空寂的大漠,一眼就望到边界上一个剪影:余晖勾勒的巨大半身人影与地面融为一体,突兀的矗立在场域中,既是超越现实的幻影又是真实的存在。在这片脱离了时间意义的存在,如同开启了时空之门,链接到未来某个遥远的时空……没有了人类的存在,社会的痕迹消除殆尽,只有这个巨大的、冰冷的躯体印证着人类文明曾经的存在。继2018年后,2019年《预言》的又一个艺术项目启动了。Ta矗立在北京中粮置地广场,这个位置正好可以俯瞰地坛,使得作品跨越了空间的界限。民勤腾格里沙漠——亘古永恒的黄沙作为自然的神秘见证,消解了时间的存在与意义;地坛——“皇地祗神”之所,暗合天地造化、乾坤奥妙,古代天人哲学的映现。沙漠之上,地坛之间,这个关于“天、地、人”的主题剧场在中国东、西两个完全不同的空间场域演绎。

景晓雷作品:《预言》
近期另一件作品《天镜》也即将落地。大地上的一个个镜面,映射不断变幻的天空,四时寒暑、昼夜交替,在镜像的虚拟空间中加入了时空概念。镜面内置激光装置,透彻而有力的光束在夜空中自地面射向夜空,是地球与穹庐宇宙之间的对话,成为地球与宇宙信息交流的介质。我希望人类文明的有限性在这里延伸出去。
现在我的创作,并非局限于一种材料,材料选择取决于作品需求。不锈钢是我现在经常利用的有形材料,随着创作的延伸和拓展,作品中的媒材也不局限于有形材料,开始尝试光、空气以及一些影像技术的介入,这些实验我都乐于一试。
范晓楠:最近你还要参加深圳的一个展览项目,据说是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与艺术的碰撞,探讨科技与未来的艺术展览,你喜欢刘慈欣的《三体》《超新星纪元》《球状闪电》等作品吗?对于你的创作有何启发?
景晓雷:深圳的这个展览项目还在筹划之中。这三部刘慈欣的作品是他最为经典的,我很喜欢。在年少时我其实就比较喜欢和科幻相关的一切,前两年还读了弗朗西斯·福山写的一本《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后果》,他谈到技术改变会直接影响社会框架,或者说是政治形式。这些都对我今天的创作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最早看的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给了我很大触动,里面的哈儿(一个人工智能机器)就是我们现在对人工智能的担忧,而书中最后几页很难理解让我至今都在思考。你能想象吗?一个作家变成了伟大的预言家!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