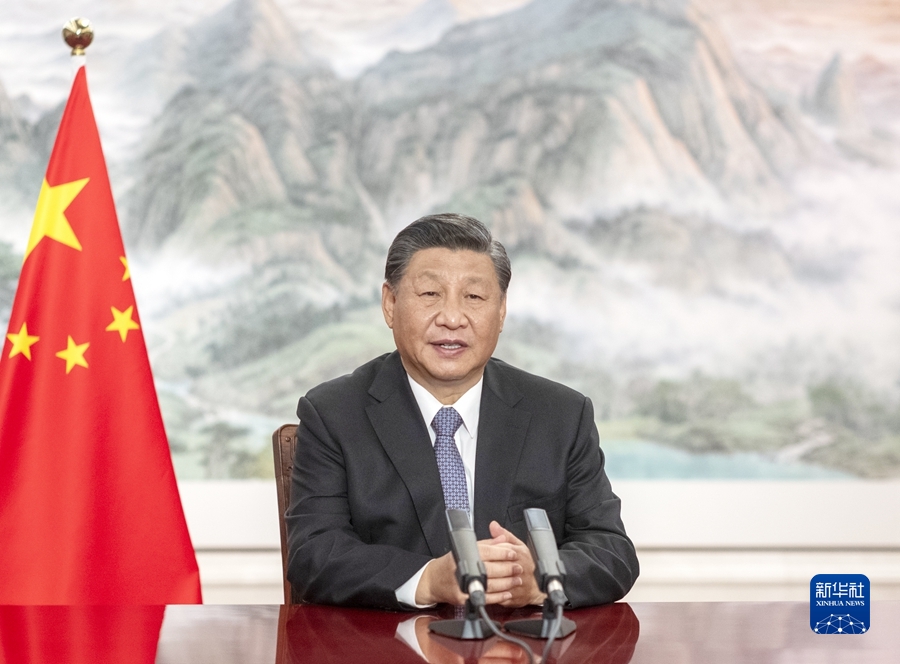形似手枪的喷雾器,汩汩而出气状的白烟,隆隆作响。全副武装的消毒公司员工,肩扛着设备,从一楼喷洒到七楼。
2月17日起,武汉市开展为期三天的大排查,希望将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以及有发热症状的四类人群“应收尽收”。
在这个位于长江西岸的老小区,“消毒”是人们最迫切的愿望。小区间或进出的救护车,身穿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滋生出各种想象,包括谣言。业主们在社交媒体上反复发帖,要求社区增加消毒频率。
尽管社区回应,许多人心惶惶的楼栋并没有病人,“请居民不信谣、不传谣”,但最终他们还是请来了消毒队。

2月17日,消毒开始了,共持续三四天时间 。
楼道弥漫着雾化的消毒水,和其他武汉小区一样,2月20日,这里进入“全封闭管理”模式。
眼下,足不出户已经多日,业主们的焦虑似乎没有解除——一面来自买菜买药之类的日常,一面来自小区里可疑的“异动”。
疫情中的一个武汉小区,正在经历复杂的情绪波折。
【一】
小区外观有些陈旧,3000多名住户里中老年人占了大半。2月中下旬,已是“四类人群”清零的最后时刻。但在小区深处的一栋居民楼,有人还是怀疑,有遗漏的病人。

该小区于2000年竣工,地处偏僻,住户多是老年人。
二楼的王凤英50多岁。她隔着纱门对记者说,物资紧张可以理解,但小区里有的事,令她心里打鼓——
小区门口有个棋牌室,老板是不到七十岁的老太太。王凤英的老公常去打牌,与他们家人很熟。女店主在年前被看见去医院吸氧,听说也发过烧。
“以前只听说她有高血压、颈椎病。她生病以后,我们反复打过几个视频电话,想问候她,全都是她的家人接电话,总说她的病还好。”
后来女店主去世了,家人说死因是急性心肌梗塞,但王凤英不信。那时,小区的微信群都在提醒不要接近病人和家属,居民们遇到会绕道走。
她很想问女店主的真实死因,但“我们不好打听哪,问的话,就像是我们要看她家的笑话”。
王凤英有两个八十多岁的亲戚,都是确诊的“新冠”患者,那时床位紧张,他们没能住进医院,1月下旬先后去世。临终时,他们才从家里被拉去急救中心,再被拉去殡仪馆。
王凤英自认还年轻。但她的同学群里,也不时有人提到同龄的朋友去世,对王凤英来说,那都是有名有姓的人,她的心止不住地震颤。
“莫得办法呀。这是一下子爆发出来的,医院收不了这么多,年纪大了,抵抗力差了呀。这个病它没有特效药,就是靠免疫力拼呀。”
在小区封闭管理前,她也不愿意迈出家门一步,要不是家人要吃要喝的话。
她两三天出一次门,回家给衣服喷上消毒水,然后挂到阳台上。她用掉了一包鞋套,很遗憾自己没“眼镜”(护目镜)。万不得已出门倒垃圾,她总是心里很慌。
说着话,王凤英往空白的楼道里扫视,也许楼上有发热病人,只是躲起来,不愿意说。她对记者说,很盼望消毒,把整栋楼都彻底喷一遍。
【二】
不时有救护车和接送病人的白色面包车停在小区门口。车辆的照片被拍下来,在业主自建的微信群里流传:有一辆白色的车子开出去了。
业主群里大多是生活信息,例如自发团购口罩和食物的接龙活动,但有时疫情“线索”也在这里流通。
听说,小区新增了确诊病例,“谁能告诉我啥时候带走的啊?”一个年轻的头像发问,“我下午稀里糊涂地在外面……谁能告诉我有没有跟(病毒)擦身而过?”
“人是在x栋x单元上的车。”另一人说。
“是有个什么车子进去,好像跟门口的人还争论了两句,我看了一眼……然后出来的时候,我在门卫室这边,露了一点头出来。”她连发了几个哭泣的表情。
业主们试图复盘小区“疫情”的起源和传播路线。
王凤英的朋友,住在三楼的江小梅肯定地说,这病是小区里的老年舞蹈队吃年夜饭传开的。她们回来后,有一部分人发烧,有的住院了。
江小梅揣摩着,舞蹈队里的一些阿姨很爱面子,她们得了病,可能“阴着”不说,平时她们和老公吵架了也不会说。
“听说有个女的老公一直在咳”,江小梅神秘地对记者说。她是个说话中气十足的老年人。江小梅一直不喜欢舞蹈队——何况,舞蹈队与小区物业走得太近,江小梅对物业又不满意。
她抱怨说,物业聚餐“抠门”,端一盆圆子上来,物业的人一下就倒走了,要带回家里。“我说这次你吃得好吧,大家全部都到医院里去了呗。”
自从病毒源自年夜饭的说法传开后,小区里有人四处打听,那张桌上,究竟坐着哪几个人。
在江小梅楼上,六楼的住户邱兰分析,好些密切接触者在外乱跑。比如,一个黑衣的女青年——她向记者展示了一张穿黑羽绒服的女性照片,但她不认识图片中的姑娘。
这样的图片也来自业主群。从居民楼往下俯拍的视角,据说是前一天拍的。图片上还有水印文字,“父亲已确诊”。

小区居民常看到救护车进出,拍照在微信群流传。 受访者供图
五十多岁的邱兰有些激动:“她爸爸已经住院了。她应该上报去隔离呀,她带着那个病毒,不是把我们所有人都害了吗!”
邱兰自己和儿子儿媳住在一起。她在疫情中费劲得到了批准,把儿媳妇平时独居的奶奶接来住。这些事搞得她焦头烂额。
有的业主打电话给社区要求全面消杀,那时正是疫情最胶着的时候,社区表示人手不够。业主们又提到“黑羽绒服姑娘”,要求社区对她进行强制隔离。
社区回复说,她父亲没有确诊,那个说法是谣言。于是业主们又打市长热线,投诉社区干部。有的业主看到病人家属出门买东西,选择了报警。
“社区说话的口吻比我们的硬,”邱兰的儿子说,“不肯管我们”,他有心脏病,一直喘息着。邱兰请记者不要担心,不是病毒。
七楼的住户王南很同情社区,他觉得社区和物业的工作人员没什么防护,就在户外工作,与医护人员一样,都是“搏命”,他不想给他们增加负担。
王南和老伴都快七十岁,他们在顶楼搞了一块菜地,日常摘些蔬菜使用,已经有一个月没下楼了。
王南说话慢条斯理的,他说自己是退休干部,原本是河南人,一直在武汉工作。他也想抱怨些什么,但终究停了下来。“要我怎么说呢,闺女。你要我说什么好呢。”
【三】
整栋楼的人都觉得消毒的事应该物业负责,而物业经理对记者说,小区有几十栋楼和十来名物业人员,其中三个看大门,两个管理,其余的是电工和保洁员。物业做不到对所有楼道进行消杀。
邱兰推荐记者去见一位热心的业主刘正凯。这是个高高胖胖的年轻人,27岁的健身教练,他自我介绍,早年爱玩,喜欢打架,现在已经改好了。
刘正凯回忆,有一天他在自家的露台上倒茶,看见一副担架抬着病人出去,他只感到一阵气血上涌,在那一瞬间,他觉得要站出来组织大家共同“抗疫”。
在健身房的不远处有家书店,刘正凯读了一本切斯特 巴纳德写的《组织与管理》。他当即制定出计划:在小区里招募年轻志愿者,最好是30岁没结婚的,40岁以下也还可以,每栋楼招一个人,统一出门采购。还要集中采购一批消毒药水,也由年轻志愿者消毒。其他时间,居民都不要出门。
这是记者见到他之前数天发生的事情。但2月13日的刘正凯有点丧气:他往小区微信群发送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然后在夜晚端着喇叭在小区里循环播放,号召居民出来参加消毒——但没有年轻人来加他的微信。
40岁的邻居姐姐想参加志愿者活动,刘正凯说,你有孩子,要注意安全,不要外出。还有几个60岁的老人也加他的微信。刘正凯觉得这与害人性命无异。他一一拒绝了他们。
后来,社区书记向记者解释,小区里本就老年人多——曾经有个活动叫“邻里关爱”,内容是60岁的志愿者给80岁的跑腿采买。以前,刘正凯从不参加小区里的社交活动,早出晚归的他只认识一个年轻邻居。
刘正凯孤独地用浇花用的小壶给自己的楼栋消了一遍毒。他觉得小区里的传言有点过分,于是独自守在大门口,记录每一日运送病人车辆出现的频率。
因为业主群流传某一户人家有还未送医的确诊病人,刘正凯决定亲自上门验证真假,他特意选择晚上,这样家中必定有人。出门前,他甚至戴上了驱邪的钟馗挂件,结果证明都是谣言,那单元房里没有住人。

刘正凯出门消毒,有些紧张。他戴了个钟馗挂件,用于辟邪。 受访者供图
“一个个都只会在群里传图片,瞎说八道。”刘正凯后来变得有些愤世嫉俗。
但是,他又能理解他们的心情。采访的第二日,他也给记者发来那张黑羽绒服女性的照片。“整栋楼的人都吓得要命。”刘正凯说,“能不能帮忙核实一下?”
他有个朋友的母亲发热,住在某栋楼的楼顶。楼下出过“新冠”确诊病人,那天晚上,刘正凯六神无主,和记者探讨是否要把病人送下楼去看病,“会经过确诊病人的门口”。
最终,朋友的母亲还是去看病了,确诊也是“新冠”肺炎。
【四】
“你跟他们很难说得通。”记者见到负责该小区的社区书记周文山时,他显得很烦闷。
“有的人投诉说物业只往楼道口洒点清水,这怎么可能?还有人要整栋楼全部消杀,物业经理说,哪怕高档小区的物业也做不到。居民能听得进这种话?”
物业一般归房屋管理局指导。周文山说,社区平时让物业做些事,靠的是私人情面。在“四类人员”“清零”的当口,周文山再顾不上居民和物业之间的矛盾。
2月13日,他正忙着劝说密切接触者去隔离点。据街道办事处的人说,周文山曾到某户居民家门口蹲了一晚——劝说是一件机械的事,是不断与人说同一套话,最后把人“哄”上车去。
“隔离是为了你的安全,也是为了你家人的安全。政府花这么多钱,都是为了你们居民好。麻烦的并不是你,你身体好,你屋里(家里)要是别人身体有点……划不来嘛,到隔离点去有吃有喝,又不要你掏一分钱。”

社区服务中心位于一条城乡结合部的小巷子里
近一半人都需要周文山反复说这一套话。2月19日,记者第二次见到他,仍旧如此。
他正接起一个电话,那一端的同事说,解释不通,有个密切接触者不想带被子去隔离点。周文山说:“那我们一下买不到嘛,你说是不是,你说能不能买到?”
酒店改为隔离点后,他们“抢着”把密切接触者送进去。否则,出现新一例的确诊,就会立刻多出许多密切接触者,又有很多变数。
武汉各区疾控中心掌握街道、社区的“四类人员”身份信息。除了各街道城管和志愿者负责开车接送,周文山所属的区要求社区干部亲自将“四类人员”送上车,完成交接。如果是确诊的病人,街道办事处要派员跟车。
于是,在2月19日下午,周文山两次艰难地将自己套入一身工业级别防护服里。他说,社区干部大多都是女的,胆子小。而他,是个55岁的男人。这一桩事要接触患者与密切接触者,如果大家轮流去,回到社区服务中心容易交叉感染。说完,他骑上一辆“社区巡逻”字样的电瓶车飞驰而去。
此前,听记者提起那个强烈要求消毒的小区,周文山脸上的烦闷又加重一层。他回忆,这小区里有个密切接触者不想去隔离点,非常难搞。
最终,他一气之下对那女子说:“你小区微信群里都在咒你。要不,你写个保证书,以后被业主打了,不要找我。”对方听了,要求立刻去隔离点。那是一个夜晚,临时找不到车辆。周文山领着她,走了2.5公里的夜路。
【五】
坐到记者面前,周文山说,正好把之前的经历都梳理一遍。
社区服务中心有十多个职员,除了一个人专门负责数据,其他人都忙些琐事。辖区内有一万多人,有的居民会提出稀奇古怪的需求。有的明明60多岁,子女只住在一公里外,可非说自己已经80岁,要社区给他送菜去。周文山内心觉得不应该,但他担心投诉。只要有居民打市长热线,甚或有直接报警的,他们都要交书面材料。
没疫情的时候,对居民提的要求,社区干部会做入户核查,一般只有无子女的孤寡老人、残疾人,才能享受特殊照顾。可是,周文山现在不愿意差人到居民家去。那些送药送菜的需求,只能先答应下来,给居民送到门口。
他说,腾不出人手去做消毒。即便有志愿者愿意去消毒、与病家接触,周文山也不会放行。这是有感染风险的事,即便志愿者不责怪他,他们的父母和朋友也会打市长热线、报警。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他感慨。
1月23日,武汉“封城”。那天是腊月二十九,有外地人到社区服务中心来,想请他开个证明。他们以为社区能批准他们离开武汉,但周文山开不出证明。他当时还想,等疫情过去,这些人能回家过元宵节的。
大年初一晚上开始,周文山住到了他位于社区服务中心二楼的办公室里,此后的二十多天,都没有回过家。他的手机总连着充电宝。春节的头几天,大量的病人家属打不通“110”“120”,就打他的电话——他的电话写在社区的公告栏里。
最紧张的时候,是正月初三、初四,他没有怎么睡过觉。那两日武汉落了小雨,到初五,就转成了雨夹雪。周文山挂了一个电话,能看见刚才没能打进来的,回拨过去,那一端是对他的哀求:我在屋里头,烧得快要死了。
但床位太不够了,他只好对病人们说,我们社区只有这点条件,我明天给你上报到街道啊。
那段时间,周文山不脱鞋睡觉,也不关灯。
有的女病人在家生病,社区里帮不到她。她的女婿先到社区服务中心来骂了一场。第二日,仍然不能住院。她的女儿跑来社区,摘下口罩,哈出一大口气。
2月2日,“松动了”。这一天开始,病人陆续住进了医院。可周文山感到疲倦万分:之前深夜来电,有发烧的人攻击他,说他不为他们服务;病床供应增加以后,甚至有人夸大病情,想赶快住院;还有的人想给周文山送钱,这让他感觉受到“侮辱”。
最近,周文山在给老年人送菜。他说送菜挺开心的,虽然爬楼累点,但老人们都感谢他。
【六】
“防护服不可能按照量来送。”街道办事处主任刘宁对记者说,“区里只是大致估计一下各街道的需求。有时候,为了省防护服,接完病人就在楼下站一会。这样能省下一套。”
省防护服的是刘宁自己。他替区政府解释,要求基层干部亲自运送病人的理由是:到了医院的接待处,病人之间为避免交叉感染会主动站得“非常分散”,需要有人维持秩序。
刘宁与负责开车的城管队员去过两次方舱医院。2月15日上午,刘宁在街道办事处的走廊里踱来踱去,给密切接触者打电话。社区书记搞不定的密切接触者,也要转到刘宁这里。
但刘宁说,他没有社区干部困难。“他们与无数的人打交道,我们只与有限的人打交道。”
特殊时期,社区办事处原有的建制打乱,分成运输组、物资组与数据组。运输组调度改装过的城管车辆,作为临时的救护车运送病人;物资组要给隔离点的患者送日用品,从区政府运回酒精和成箱的中药,再分发到各个社区;数据组实时更新各社区的病例情况,包括体温、核酸检测结果,每个确诊病人的密切接触者。
数据组的王佳在区疾控中心的微信群里。最忙的时候,群里会在深夜跳出信息,说是某个医院有床位,请各街道上报病人最新情况。王佳忙不迭地给区疾控发邮件,包括辖区内重症患者的个人信息和胸片。王佳总觉得,自己在与其他街道比拼手速。
那段时间,为了确定上报名单,刘宁和王佳要给各社区上报的重症病人排队,分出轻重缓急。刘宁说,各个社区书记在材料里的口风不一样,有的特别紧张,有的可能在辖区里收集到太多病例,描述时反而轻描淡写。
一开始,刘宁会找街道卫生中心的人看一下胸片,但后来中心主任染上“新冠”病毒,就再没有多余的医生帮他干活。
刘宁是哮喘患者,“对咳喘的事比较了解”,于是他自己给重症病人家属打电话。有时候他也会想,错了怎么办,“那只能尽力而为吧”。
他说起一个35岁左右的“新冠”患者,有哮喘的基础病,“我还好,”病人在电话里说,“把床位让给其他人吧”。
过了一会,病人的妻子给刘宁打来电话,边说边哭。其实这个病人的情况不太好。后来,刘宁把他送去了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
方舱医院刚开始收治病人时,有几天,接收重症病人的定点医院还比较满,刘宁想让辖区内的病人都及时住进医院。
“住进方舱要测静态血氧饱和度,”刘宁回忆,“我就和病人们讲,去的路上平心静气一点,不要急躁,一躁血氧饱和度会下跌。”
2月15日,刘宁有一件事想和区政府汇报:辖区内有一名不到30岁的尿毒症患者,核酸检测阴性,但属于符合临床诊断标准的“新冠”病人。他不愿意去方舱医院,理由是不方便去另家医院做透析,而且有交叉感染的风险。刘宁想问下区里有没有折中的办法。
他的另一桩任务是筹备封闭小区。在刘宁的辖区内,不少居民楼的楼栋直接面向马路。只好组织一下,把马路也封起来。

街道办事处主张封锁马路,这天下雪,要趁路面结冰做完。
千头万绪的事等着他们去做,消毒只是其中一件。
“疫情”暴发以后,只要是有人在家死亡,无论是否有迹象显示与“新冠”有关,都要对房屋内部进行彻底的消杀。坐在王佳斜对面的郑云,就负责收集社区人员的去世信息,对接区疾控去消毒,给他们协调车辆。
她还负责核对密切接触者。当一个病例确诊后,区里会先找病人了解情况,然后把密切接触者的名单发送给她,她打电话复核后,重新上传。过一段时间,区里会给王佳一个确定版本的密切接触者名单。王佳再把名单分发给各社区,说服他们接受隔离。
但作为“其中一件”的消毒,此刻在居民眼中无比紧迫。
刘宁交办郑云,联络下可以做小区外部消杀的第三方机构。在前述工作的空隙,郑云打了几个电话,第一个说自己正在隔离点干活,第二个关机,第三个说,消杀一栋楼的价格是700元。郑云觉得有一点贵,她拿不准由哪项经费出这笔钱。
【七】
消毒前后用了三四天,里里外外雾气滚滚。
“现在居民也比较怕,要让他们有安全感嘛。”19日的采访中,周文山说,他劝服了物业经理,掏钱搞一次消毒,要不然,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小区已实现封闭管理了。2月20日,物业张经理在协调给小区居民买菜。他对记者说,别老听着居民骂我们,这个小区每年的物业费,不过每平方米6毛钱,这点钱能干什么事?

完成“四类人员清零”以后,社区的主要工作是保障民生。大门口堆放着萝卜和冬瓜。
疫情之中,物业倒下了一个电工。他大约52岁,高高瘦瘦的,武汉黄陂人,他的老婆也得病了。看门的大爷说,居民之前看见电工出门就很紧张,为此报过警。
至于那个身穿黑羽绒服的年轻女性,在街道办事处的文档中,她的母亲在1月30日住进医院,是确诊的“新冠”病人。她的父亲在2月2日左右也开始发热住院,但核酸检测阴性,也不是临床的疑似病例,最近被定性为普通发热,已经出院了。所以,黑衣的姑娘不算是密切接触者。
小区里长期分成支持物业与反对物业的两拨人。江小梅经常与物业争吵,2月20日,当记者再次见到她时,她抱怨说,消毒的时候只听到隆隆的响声,闻不到84消毒水的气味,担心是走形式。但她又说,现在觉得,物业也很不容易。
转变的起因是,小区封闭后,开始招募团购志愿者。江小梅想撺掇其他反对物业的姐妹去报名,正好让物业看一看,她们是怎么管理这个小区的。可那些姐妹又不愿意。江小梅很不忿。她想自己去当志愿者,外出替居民采购。
邱兰还是惴惴不安。她对记者说,前一天小区微信群里还有求助的,是有个女人,已经喘不上气了,住在楼上的王南为此报了警,后来又说不是“新冠”。邱兰搞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但王南向记者解释,他没报警,只是打了市长热线。过了一会,社区回复说,求助帖不是本人发的,是那个女人的朋友代发的,朋友在电话里听女人气喘吁吁的,就报警了。实际上,女人家里的确有“新冠”病人,但14天之前已经送医,她也不算密切接触者。
小区出门左拐是个大卖场,三个中年男人站在门口,阳光打在他们的脸上。他们都是小区的团购志愿者,在等着搬运各类货物。其中一位说,小区不招募志愿者了,人再多一点,就变成“人群聚集”。
刘正凯最终没参加这次志愿者活动。他觉得,自己之前在外购买消毒物品,又拿大喇叭在小区招募志愿者,接触太多,需要在家自行隔离。
可在家待了几天之后,他在微信上吐槽,“我好无聊啊”。经过朋友介绍,他决定去当治安志愿者了。
2月22日,他的任务是去方舱医院附近巡逻,夜班,晚上6点开始。
出发前,刘正凯有点紧张,他担心有坏人冲他吐口水。但是,“没关系,我会综合格斗,要是有人敢在夜里做坏事,我就去抓这些坏人”。
他戴上了他的钟馗挂件。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