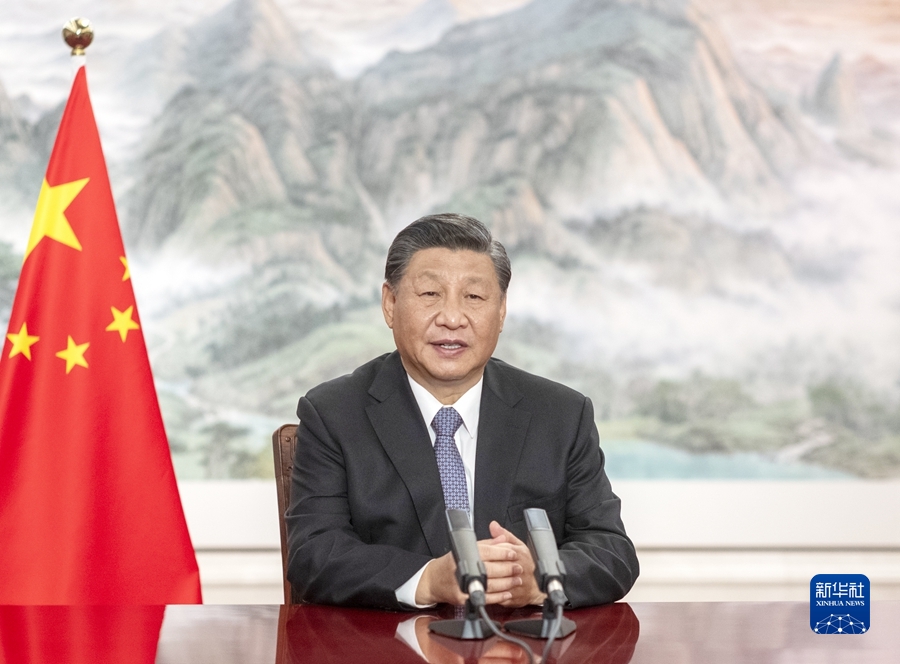不管是汉唐,还是宋明,大臣写进呈皇帝的奏疏时,都是自称“臣”。惟独清王朝是个例外——如果我们去读清朝人的奏折,便会发现,他们总是自称“奴才谨奏”、“奴才跪奏”;接到皇上的圣旨,则赶紧表态说:“奴才跪诵之下不胜悚惧无地自容”,“奴才伏读再三更切悚惶”。
称“臣”与称“奴才”,意义有什么不同吗?
当然。
有人说,奴才的地位比臣更卑贱。这么说有点望文生义。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清朝人都能够称奴才,称奴才是需要资格的,只有旗人才可以称奴才,汉臣想要称奴才都不让。旗人的地位怎么可能比汉臣更卑贱呢?虽然乾隆皇帝曾说,“盖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属一体,朕从不稍存歧视。不过书臣觉字面冠冕耳。初非称奴才即为亲近,而尽敬称臣即为自疏而失礼也。”标榜臣与奴才一视同仁,但这话显然属于“此地无银三百两”,正好证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称奴才才跟皇上更亲近,称臣则显得疏远。怪不得大清臣子要争先恐后地自称奴才,以成为皇上的奴才为荣。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奴才的地位其实比臣更尊贵?也不是。试想象一下,一群原来称臣的官员,争着称奴才,难道就是地位更尊贵的表现?清史研究方家杜家骥先生说,清代汉官自称奴才,是“自贱其身”,往代汉族士大夫的那种廉耻观念与刚直气节在他们身上丧失殆尽。这个评价是有道理的。
清朝旗人自称的“奴才”为满语“阿哈”(aha)的音译。阿哈即奴才、奴仆之意。清人入关之前,阿哈与主人是常见的社会关系,因为女真部落还保留着草原奴隶制的遗存,八旗体制便是一种主奴体制,旗人中的包衣、旗下家奴,法律身份均为家奴,包衣隶属于天潢贵胄、王公贵戚,是皇室、贵族的家臣;旗下家奴隶属于一般的正身旗人,是法律上的贱民,没有独立户籍。不管是包衣,还是旗奴,他们的家奴身份都是世代相承的。

旗奴在主家面前,自称奴才。包衣在自己所隶属的宗室贵族面前,也是自称奴才。奴才,本质就是人身隶属于另一个人的私民,代表一种人身上的依附关系。
其实,汉语中的“臣”,原本也表示一种人身上的依附关系。在甲骨文中,“臣”如束缚之形,意即“奴虏”。《尚书正义》注释:“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章太炎考证说,“臣本俘虏及罪人,给事为奴,故象屈服之形。”也就是说,从字义的本源来看,“臣”与“奴仆”是同义的。在甲骨文时代(殷商时期及之前),臣就是奴仆,奴仆就是臣。乾隆皇帝称“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属一体”,并非没有道理。
然而,到了周代,附着原始奴隶部落制度的瓦解,“臣”字已经摆脱了原始的意义,不再指奴仆,而是指君主任用来治理国家的官僚。《说文解字》称,“臣,事君者也。”《礼记·礼运》称,“仕于公曰臣。”
虽然臣为“事君”之人,理当效忠于君,但经过先秦儒家的阐释,臣并不是君之私仆。君臣关系因而是一种权利—义务对等的合作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首先要像个君的样子,臣才有效忠的义务;君若不君,则臣可以自行解除效忠的义务,“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是孔子赋予君臣关系的新内涵。
孟子的君臣思想比孔子还要“激进”。他认为,对于异姓之卿来说,“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而对于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意思是说,如果君不君,则臣可批评,如果君不听,则异姓之卿可自行解除君臣关系,贵戚之卿更是可废掉君主,另立新君。甚至,孟子还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也就是说,经由孔孟的阐释,甲骨文时代的私人性主奴关系已经演变成儒家时代的公共性君臣关系。自此,臣应该服从的,与其说是君主,不如是说自己信仰的道,“从道不从君”,用宋人的话来说,“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

虽然秦制建立后,出现了君尊臣卑之趋势,但历史发展到宋代时,士大夫地位达至历史高位,形成典型的士大夫政治。士大夫自我期许为治理天下的主人翁,自认为“士当以天下为己任”,并且向皇帝说“君主当与士大夫共天下”。而宋朝皇帝也不能不同意。这个时候,你要是说臣是君的奴仆,宋朝士大夫宁可一头撞死。
清朝皇帝要求旗人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是想强调皇帝与旗人之间,是一种“你属于我”的主奴关系。汉人争着自称奴才,也是想向皇帝表明心迹:我也您的人哪。
从臣变成奴才,意味着先秦以降的有着“从道不从君”内涵的公共性君臣关系,退回到部落文明形态的强调人身依附的私人性主奴关系。从甲骨文时代到孔孟时代的千百年文明演进,算是白费功夫了。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