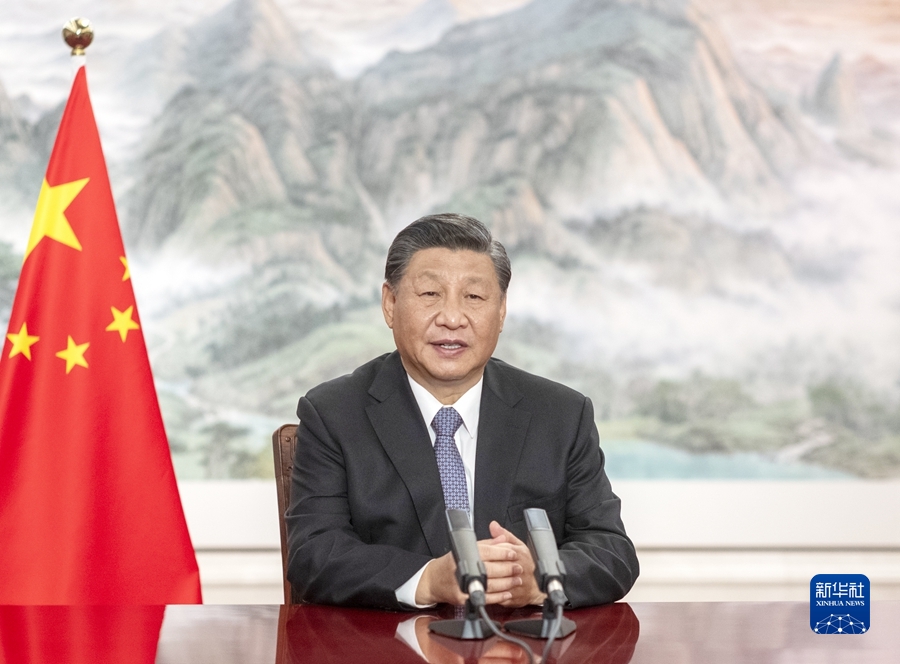前言
明诗坛于诗史不振,业已成学界公论。概此一带,不但有前后七子的“欲使天下人不读唐以后书”的拘泥复古,也有台阁诸公千篇一幕的泯灭灵性。非如此,在日益式微的明诗坛中,诸巨擘尤好为把持文脉而别有心肠。

其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同为明诗坛领袖、七子发倡者李攀龙、谢榛的断交公案------毫不客气的讲,二人的断交并非仅是因诗论而“道不同不相与谋”,更多的是整个明诗坛中政以侵诗的龃龉。以下,笔者便浅以论之。谢榛格格不入的“布衣山人”身份
李攀龙曾赠谢榛诗云:凤城杨柳又堪攀,谢朓西园未拟还。客久髙吟生白髪,春来归梦满青山。明时抱病风尘下,短褐论交天地间。闻道鹿门妻子在,祗今词赋且燕关。《初春元美席上赠茂秦得关字》(明·李攀龙)
订交之初的情谊时,也点出来了谢榛为人为诗的几个特点,一是"短褐",即其身份为布衣;二是"论交天地间"即交游广泛;三是"鹿门",即其志趣为山林。从这三点恰恰也可以看出一些"不合"的兆头来。

以布衣山人之身,侧身郎署官员之间,于体不宜,
诗佚事丨于明诗坛厥功甚伟的谢榛,为何除名于“明七子”之外?一已述,兹不赘言。
谢榛交游广泛,诚不虚言,检点其诗集,谢榛所赠所述之人竟能逾千,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布衣平民,无所不包。不择好恶的朋友结交多了,有时并不是一件好事,对于一介布衣来说可以无界限地结交朋友,但对于一个"诗学团体+政治团体"就不可以了。上文说到,七子大都属郎署官员,是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比如王世贞就和权臣严嵩有着血海深仇。

父忬以泺河失事,嵩构之,论死系狱。世贞解官奔赴,与弟世懋日蒲伏嵩门,涕泣求贷。嵩阴持忬狱,而时为谩语以宽之。两人又日囚服跽道旁,遮诸贵人舆,搏颡乞救。诸贵人畏嵩不敢言,忬竟死西市。(《明史·王世贞传》)
再如七子之一宗臣:起故官,移文选。进稽勋员外郎,严嵩恶之。.......杨继盛死,倡众赙送,忤严嵩。(《明史·宗臣传》)
谢榛却似乎与严嵩有些交往:壬戌岁,严阁老嵩罢归江南,会诸缙绅谈及河套不可复取,曰:"谢四溟山人独有先见。"此闻之邹处士伦云。嵩论与鄙见略同,然借此成曾夏二公狱,另有史氏之评。(《四溟诗话》)
谢榛作为一个布衣,必须得依靠四海结交的朋友才能生活,要让他完全站在七子的政治立场上,实在有些勉强。所以李攀龙在绝交书里不止一次地讥讽他结交贵人:时尔实有豕心,不询干我,非其族类,未同而言,延颈贵人,倾盖为故,自言"多显者交,平生足矣"。尔且以敝邑之顽民,行而即长安贵人谋我,天诱其衷,元美弗二,尔是以不克逞志于我。(李攀龙《沧溟集·戏为绝谢茂秦书》)

从这一段看,谢榛似乎还曾用计离间过七子的内部关系,因为李攀龙引用的是《左传》名篇《吕相绝秦》的典故。但这里"长安贵人"是谁,"元美弗二"是怎样一件事情,笔者没有考证到,就不加详述了。但它严重损害了谢榛与余子的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左传·成公十三年》)李、谢诗学理论的分野
下面再来谈谈李谢二人诗歌志趣、持论的问题。神韵与格调
谢榛著诗话四章名为《四溟诗话》又名《诗家直说》,所谓"直说"便是要显露"天机","天机"便是诗文创作的规律。谢榛是一个近乎纯粹的诗人,他眇目、布衣,但却一直致力于揭露诗文创作的规律,这一点与李攀龙显然不同,李攀龙曾就此批评过谢榛:己酉岁中秋夜,李正郎子朱延同部李于鳞王元美及余赏月。因谈诗法,予不避谫陋,具陈颠末。于鳞密以指掐予手,使之勿言。予愈觉飞动,亶亶不辍。月丁乃归。于鳞徒步相携曰:"子何太泄天机?"予曰:"更有切要处不言。"曰:"何也?"曰:"其如想头别尔!"于鳞默然。(谢榛《四溟诗话》)

这里倒显得李气量不如谢了。但泄不泄露"天机"还在其次,他们每个人所理解的"天机"吻不吻合才更加重要,因为一个社团的理论要想坚牢,内部社员的持论就不能差异过大。
从前面那首诗,我们得出谢榛的志趣为山林,这是不错的,这也和他的布衣山人的身份相符合。检阅谢榛的诗集,扑面而来的将是大量的"山林"诗,这源于悠久的"山人"传统,他们热衷于山清水秀、热衷于花草鸟木,所谓"山林一身重,钟鼎几人轻。"(谢榛《寄孔方伯汝锡》)是也。而翻开李攀龙的集子,则扑面而来的是雄壮的气氛,好用大词、鲸句,所谓"大漠清秋迷陇树,黄河落日见秦城。"(李攀龙《送汪伯阳出守庆阳》)是也。

如果前以唐人相类比,谢诗更近于王维、孟浩然(这也是我所谓"山人"的诗学传统),追求的是"飘逸"的韵味。而李攀龙则更近杜甫,字字沉着,句句有力,追求的是一种"雄浑"的格调。
如果后以清人格调、神韵、性灵、肌理四说来相套的话,谢诗显然更倾向于神韵,李诗则是当仁不让的格调派。

因为李攀龙评诗"少见笔札",我这里用王世贞的较为成熟的理论来对谢榛诗风加以评价,藉此彰显他们理论上的龃龉。比如对王维、孟浩然,王元美认为他们诗好是好,但是要么"调不甚响",要么"格调非正":王维李颀虽极风雅之致,而调不甚响。孟襄阳"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韦左司"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虽格调非正,而语意亦佳。(王世贞《艺苑卮言》)
其次对谢榛的评诗眼光表示怀疑:谢茂秦谓许浑"荆树有花兄弟乐"胜陆士衡"三荆欢同株",此语大瞆大瞆。陆是《选》体中常人语,许是近体中小兒语,岂可同日!
又云:“谢茂秦论诗,五言绝以少陵"日出篱东水"作诗法。又宋人以"迟日江山丽"为法。此皆学究教小兒号嗄者”(王世贞《艺苑卮言》)
再次对谢榛本人的诗作表示不屑,甚至说出了"何不溺以自照"这样刻薄的话:谢茂秦的来益老誖,尝寄示拟李杜长歌,丑俗稚钝,一字不通,而自为序,高自称许,甚略云:"客居禅宇,假佛书以开悟。暨观太白少陵长篇,气充格胜,然飘逸沉郁不同,遂合之为一,入乎浑沦,各塑其像,神存两妙,此亦摄精夺髓之法也。"此等语何不以溺自照。(王世贞《艺苑卮言》)
在《艺苑卮言》的第五卷中,王元美对他的同代诗人进行了详尽的评述与比喻,不妨来看看他是如何评价李谢二人的:
李于鳞如峨眉积雪,阆风蒸霞,高华气色,罕见其比;又如大商舶,明珠异宝,贵堪敌国,下者亦是木难、火齐。谢茂秦如太官旧庖,为小邑设宴,虽事馔非奇,而饾饤不苟。(王世贞《艺苑卮言》)

李谢二人持论、风格不同,大略如此。再益之二人性格都是极自负、极傲慢的,持论不同更不能折中求和。攀龙既归,构白雪楼,名日益高。宾客造门,率谢不见,大吏至,亦然,以是得简傲声。(《明史·李攀龙传》)
曾有人请李攀龙看诗,李是能直接说出"夜来火烧却"的人。李攀龙的"夜来火烧却"和王世贞的"何不溺以自照"都表明七子其实是一个极具排异性的团体,他们所排斥的不仅仅是曾是社员的人,还有广大持论相异的人,不然就说他们是"宋学"。谢榛被他们"力相排挤"过,王慎之也被他们"力排之",这都很能说明他们的排异性:摈先芳、维岳不与,已而榛亦被摈,攀龙遂为之魁。其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诸子翕然和之,非是,则诋为宋学。(《明史·李攀龙传》)结言
李、谢断交的因缘,其实也算是文学发展的必然。有唐之时,虽各家诗风相异,却并无互相倾轧、是己非彼之风,大约是唐时社会风气较为开放,是比较能求同存异的。下逮有宋,则始有互相排挤的风气(江西与江湖的分野),再至明清,宗分派别,数不胜数,党同伐异之风,可谓代而愈甚。这虽不是本文所主要分析的,但从谢榛被摈、李谢断交,也是能管窥一二的。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