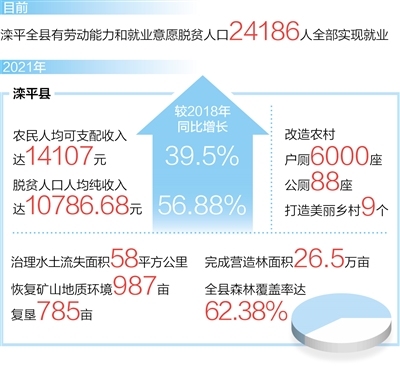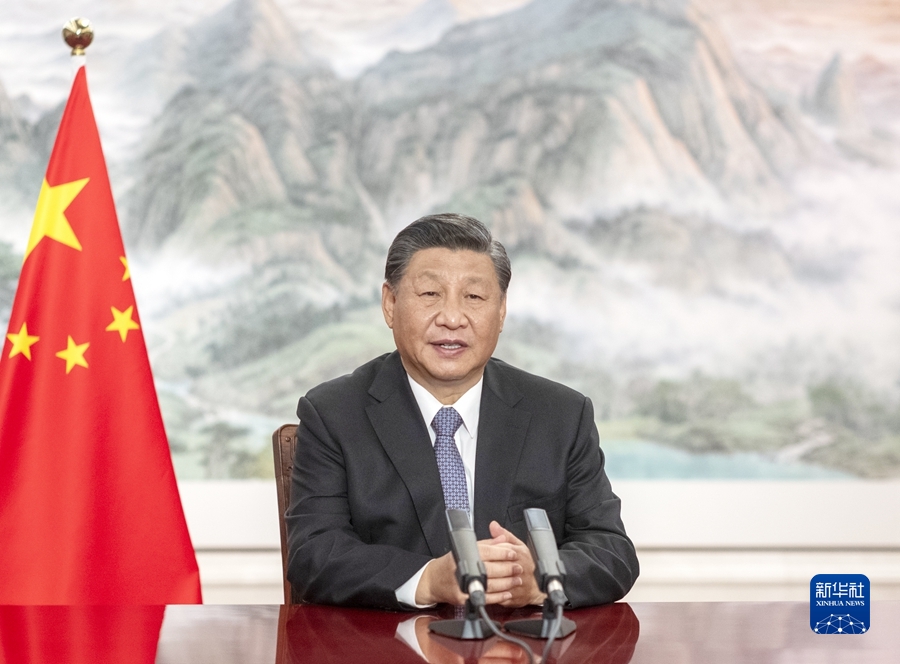唐传奇里有一个著名故事,叫作《李娃传》,作者是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

白行简塑像
《李娃传》讲的是一个姓郑的书生前往长安参加考试,对平康里的李娃一见倾心,结果花尽盘缠,被老鸨设计赶出门去。郑生身无分文,只好去负责殡葬仪式的凶肆居住,没想到却因为歌喉清亮,反而名声大噪。郑生父亲得知之后,勃然大怒,将儿子打残抛弃,沦为乞丐。李娃不忍,将郑生接回家中悉心调理。后来他科举及第,父子和好如初,李娃也被封为汧国夫人。
这个故事我一直特别喜欢,甚至可以推为唐传奇中的第一。不过不是因为男女主角,而是因为这篇文章很难得地把视角放在了长安城的最底层。

中国的古典作品,多是聚焦于帝王将相、文人雅士,偶有破落书生,也必有状元及第的一天。所以我们读那些作品时,如读神仙,漂浮于云端,高来高去,哪怕是权谋宫斗的戏码,也是发生于深宫彩殿之中。

至于那些生活在中下阶层的普通人,几乎没什么存在感,只偶尔作为陪衬出现。

白居易有名作《卖炭翁》,他这个弟弟白行简也不一般,在《李娃传》里不吝笔墨,在郑生、李娃的爱情故事之间,还有余力去展现一个贱业和一群贱民的生存状态。


凶肆负责为老百姓提供丧葬类的服务,在古代属于贱业,社会地位也就比乞丐好一点。别说达官贵人,就是寻常百姓也都避之不及,嫌他们晦气。可如此卑微的一个行业,同样有它自己的运转规则、生活趣味,甚至有它独特的审美标准。
《李娃传》里写道,郑生被老鸨抛弃之后,绝食生病,几乎要死,结果被屋主嫌弃,直接扔到了凶肆里头。而那些凶肆中人发现这个奄奄一息的废人之后,第一个反应是:“共伤叹而互饲之。”这些脚踏阴阳两界的人,反倒比外间更有人情味。
郑生在这些人的帮助下,奇迹般地痊愈了。
凶肆不嫌他拖累,反而给他找了一份勉强能糊口的差事,“令执穗帷”——在唐代长安城的葬礼上,灵柩之前要挂起三道穗幕,供人吊唁。“穗”是疏松的粗麻布,和丧服是同一种布料。这种帷幕非常软,需要有专人在后头支撑,一天下来很是辛苦。郑生干的就是这么一个活儿。
这不算啥好工作,但至少有工钱可拿,勉强糊口。为了这么一个半死不活、缺少技能也没什么价值的废人能有尊严地活着,凶肆也真是仁至义尽。

接下来的事情,有意思了。在当时的葬礼上有一个习俗,灵车移动时,需要有人手挽绳索牵引前行,而且要边走边唱,谓之“挽歌”。这是从汉代就传下来的古老风俗,要求唱挽歌的人一要长得清俊好看,二要歌喉婉转,能唱出悲伤的味道来,最好能把周围的人都唱哭。陶渊明有四句特别有名的诗:“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个“他人亦已歌”,即是挽歌。
挽歌的曲目有很多,有《薤露》《蒿里》《虞殡》《白马》等,都是多少年传下来的曲子。郑生是个天生的歌手,有一副好嗓子。他每次参加葬礼,一想到自己的遭遇便悲从中来,与挽歌之间产生微妙的共鸣,久而久之,居然学会了,而且比谁唱得都好。凶肆一看,这是个人才啊,赶紧给他换了个岗位,专唱挽歌,唱得有多好?——曲尽其妙,虽长安无有伦比。
连长安城里都没人能比,可见称为天下第一也不为过了。
别看凶肆卑微,这个行业的利润还不少。有钱赚,自然就有竞争。白行简特意描写了一段凶肆之间的竞争状态。当时两大凶肆,一东一西,要么是比拼硬件,看谁的车舆器具做得精美,要么是比软件,看谁家的挽郎歌喉好听。

东肆的硬件没问题,就是软件不如西肆,如今得了郑生这么一个宝贝,便暗中精心培养,然后向西肆发起挑战,要公开拿五万钱来赌斗。
要说当时的长安城,真是一座八卦之城。两个殡仪馆的争胜,居然成了大新闻。街道上报给派出所,派出所上报给公安局,最后官府居然批准这两家在天门街公开决斗。

天门街就是朱雀大街,是位于长安城中轴线上的宽街,是最宽阔壮美的一条街道。比赛当天,整个长安城的人全来看热闹了,“四方之士,尽赴趋焉,巷无居人”。

东肆先是陈列出各种华美精致的舆乘,西肆自愧不如,但他们在挽歌方面有强项,派出了一个长髯男高音,登台高唱《白马》,博得满堂喝彩。

这个时候,东肆的秘密武器郑生出场了,他的出场绝对经过精心设计,“乌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翣而至”。乌巾是隐居不仕者特有的装束,低调内敛,而翣是一种长柄羽扇,一般由侍从左右手执,但往往用于棺饰。这个排场,可谓先把气氛给调动起来了。

郑生选择的曲目是《薤露》,这是诞生于西汉的一首挽歌。薤其实就是藠头,薤叶上的露水很容易晒干,就好似人生一样短暂。可露水次日早上还能再聚,而人生却再也不可能重来了。

郑生选择的唱法,是“申喉发调,容若不胜”,没上来就飚高音,而是缓缓而起,徐徐营造氛围。大家这才明白过来,这是唱丧歌比赛,又不是中国好美声,不是调门高就好,还得看能不能把人情绪带动起来。
郑生这一手挽歌唱的,“曲度未终,闻者欷掩泣”,全场都哭了。西肆之主乖乖扔下五万钱,狼狈离场。
郑生一战成名,成了长安城炙手可热的网红,然后就是他爹恰好来长安出差,发现自己儿子不务正业,怒而鞭打……当然,这就是后头的情节了。
总之,读完《李娃传》这一段情节,能发现长安城原来有这么有趣的一面。在那些光鲜亮丽的城垣宅邸之间,原来还生活着这样一群卑微而鲜活的人。

他们的绝大部分生活根本不会被人记录下来,可从这一小段记载中,仍能感受到一种澎湃的活力。
唐传奇里讲神仙、讲官员、讲书生、讲贵族、讲名妓,可讲这些琐碎行业的却很少。感谢白行简的妙笔,给丧葬业揭开了一角,便已有如此强烈的魅力。
这让我们忍不住揣测,长安城百业百姓之中,到底还隐藏着多少被历史遗忘的故事。那么多维度、那么多细节叠加在一起,锻炼切削,方才做出一座拥有丰富质感与温度的天下长安。
根据考证,《李娃传》并非白行简原创,而是取材于当时的民间故事《一枝花》。我相信关于“凶肆”的桥段,应该在民间版本里就有,白行简不过是将其重做渲染。只有老百姓自己,才能想得起来老百姓生活中的趣味。

这一段接地气的“凶肆”描写,促成了我后来撰写《长安十二时辰》的主题动机。我让主角张小敬做了这样一段独白:
“我在长安城当了不良帅九年,每天打交道的,都是这样的百姓,每天听到看到的,都是这样的生活。对达官贵人们来说,这些人根本微不足道,这些事更是习以为常,但对我来说,这才是鲜活的、没有被怪物所吞噬的长安城。

在他们身边,我才会感觉自己活着。为了这些微不足道的人过着习以为常的生活,我会尽己所能。我想要保护的,是这样的长安。”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