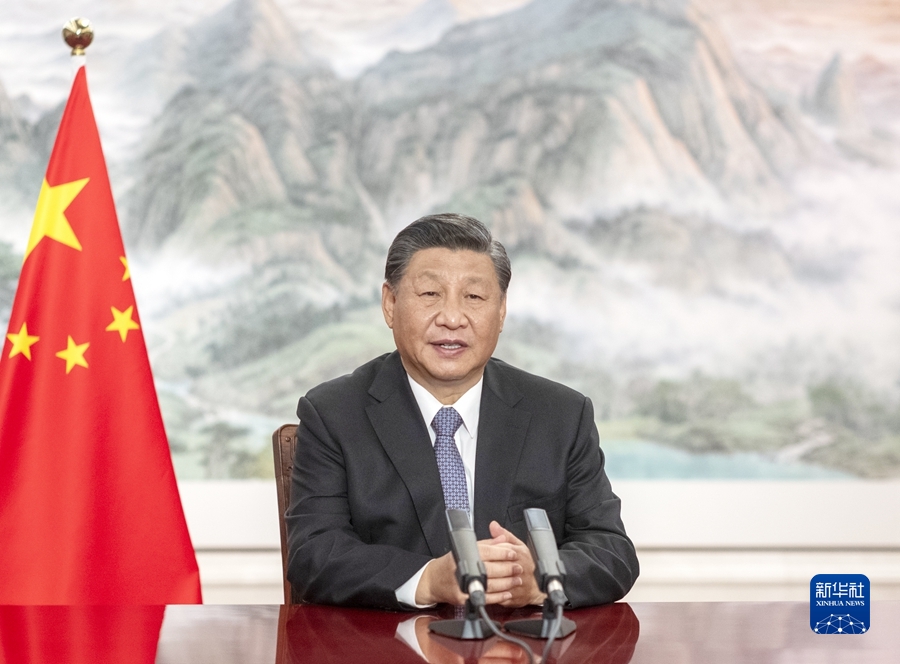普仁医院的 疫中一月
从收治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到今天,北京市普仁医院的隔离病房已经开设了整整一个月。
这里没有喧嚣的口号、表态,有的只是扎扎实实、点点滴滴的服务与奉献。改造病房;凑寻防护服;下班后还陪患者聊天;医护、清洁工、修理工、心理咨询师,人人都成了多面手;隔离结束后不打算回家仍惦着去“大急诊”;反复为痊愈患者做出院检测……

普仁医院的新冠肺炎病人转入通道(右)
没想到真的会 这么快收治病人
在1月20日左右,院领导层就已经听说可能会把东城第一家定点医院设在普仁,但院长曾文军坦率地说,“当时没有想到这么快就真的会收治病人,至少感觉还有时间做更充分的准备。”
尽管还是没有负压病房,尽管那栋SARS后改造的独立病房楼早已成为医院骨科病房和康复区,普仁医院还是认真开始了应对新冠疫情的准备。为此,他们参考SARS和湖北疫情,紧急研究出了一个需要500万元投入的病房改造方案。
然而,没过几天,这个方案就失去了意义——“根本来不及了”。
春节前为龙潭庙会做应急医疗准备、成立应急小分队,一直是普仁医院的惯例。然而2020年的大年三十下午,北京市宣布取消庙会。
普仁医院主管医疗的副院长郝宇红说,那时,是真真切切地意识到:事情严重了。

医护人员报名进入隔离病房工作的微信截图
果然,大年初二一早,医院管理层全部被召回医院——通知紧急要求医院马上开工改造病房,组织进入隔离病房的医护人员,最迟初六就要具备收治病人的条件。
1月30日,第一例新冠确诊病患从同仁转入普仁医院隔离病房。
这一天的上午,医生护士们和院里的工人师傅,才刚刚用透明胶带,把14间隔离病房的空调出风口一一封口完毕。
意识到不久前做出的500万元改造方案已然不可能实现之后,从大年初二到初六这短短几天里,普仁医院那栋独立的二层病房楼里,一片繁忙——
原来的骨科全部撤离,将隔离病房与原骨科康复区的通道封死;原来的病床全部重新调整,按照传染病病房要求,布置成单人间和双人间,疑似病人单间收治,确诊病人可双人间收治;病房的门锁按隔离要求换成“外锁”,所有窗户也临时加装固定器,改成无法全开的,防止病人失控引发安全问题……
对于这次新冠疫情来说,普仁这栋十几年前改造的病房楼虽然已经显得老旧,但在这几天的时间中,全院集中人力和智慧,仍然勉力规划和布置出了一个具备污染区、半污染区、清洁区和患者通道、医护人员通道、包含清洁物资出入口和医疗垃圾出口的传染病病房。

2月的第二周,普仁医院隔离病房的14张病床一度全部满员。
开着救护车四处找防护服
院长曾文军说起最初筹备的日子,语气中仍然带着紧迫感。“从大年三十开始,我们一边紧张布置隔离病房、招募和紧急培训医护小组人员、一边满脑子焦虑着一件事,那就是,眼看就要收治病人了,院里当时却仅有20套防护服。我拿什么保护我们冲锋陷阵的工作人员啊!”
除夕、大年初一、初二,每年最重要的假日,却成了她今年最焦心的几天。“自从听说湖北的疫情,我们就开始跟常年合作的供货商联系,订购了一批防护物资,包括防护服和口罩等等。但是没想到紧要关头,却听说这批防护用品无法送到,被‘扣’在外地某市了。我们后勤副院长王效暾和器械科科长王海军都急眼了,没办法,我们决定自己跑趟该市去提货。考虑到当时交通已经受限,我们决定开救护车去。其他人同时分头联络任何可以联络的渠道,寻找防护物资。”
“结果提货的救护车走到半路,就有消息说另外一批防护物资正停留在平谷区顺丰的基地,我们的人一商量,当即掉头直奔平谷。到了顺丰物流基地,我们的人在顺丰人员的帮助下,直接进到集装箱,一点点翻找,终于找到了我们订的防护物资。”随后他们又连夜去到天津,提取了另外一批物资。
尽管区卫健委也尽力为定点医院调配了一些防护品,但要满足需要,仍然差很多。“1月28日,我们医院组织援鄂的五人医疗队临近出发。按援鄂一个月、每人每天两套防护服来算,我们算计着怎么也要给他们带够300件防护服啊,可当时我们四处找来的防护服全凑在一起,才200多套,都不够给援鄂小组带的,更别提本院隔离病房需要的了。”
“一说去一线,我们的医护人员报名特别主动、特别诚恳,可我作为院长,最担心的就是不能给他们提供最要紧的防护。”
这种焦虑,总算在2月2日时得到了缓解——“那天晚上突然接到消息,说海关有一批140箱社会捐赠的防护物资,可以调配给我们,我们当夜就跑去,全给拉回来了。”
交流靠“喊话”加微信安抚病人
从崇文门外大街东侧邻街的正门进入普仁医院,需要穿过整个门诊大楼,进入医院东院,再穿过停车场,才是独立的两层隔离病区楼。
这栋楼单独开有两个小门直接朝向医院外的西花市西街,南侧标注“发热门诊”的小门,供前往发热门诊的人就诊出入;北侧标注“肠道门诊”的小门上贴有白纸黑字“转入通道”,从隔离点或外院转来的新冠疑似或确诊病人,就由此下救护车,直接进入隔离病房,不需要经过医院的其他区域。
首批报名进入隔离病房照护新冠肺炎病人的主管护师金莉记得很清楚,1月30日晚上8点多,她穿好防护服,来到“转入通道”的小门边,等候普仁医院接诊的第一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穿着防护服,不可以走出门外。专门转运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护车停在门外,司机也穿着防护服,我们之间说话必须大声喊,否则听不见。”事实上,没过几天,金莉和她的同事们嗓子就都哑了。金莉记得,这位女患者刚到的时候几乎没有明显的症状,“有点发烧,鼻塞,真没什么症状,看上去只是有点感冒的样子。”
她是湖北人,1月22日到北京来看朋友,29日开始发烧,到同仁医院看病,很快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第二天就转入了普仁医院。
虽然她的症状很轻,但她的朋友和朋友九十多岁的父亲,没几天也进入了普仁医院隔离病房,并很快发展为重症,转到佑安医院继续治疗。
“她进来的头几天特别焦虑,先是不断说自己没病,就是普通感冒,后来认识到自己已经确诊了,就特别担心她的朋友父子俩,特别愧疚。这家人的保姆后来也住进来、确诊了。”
金莉眼看她一天天焦虑不安,但在病房里穿着防护服又不方便和她更多地交流,于是她让病人加了自己的微信:“病房里不允许我们带手机,但是等我下班了,拿到手机后,你有什么事都可以发微信跟我说……”
这位患者经过24天的治疗和观察,终于在2月22日从普仁医院隔离病房治愈出院。

不想回家,直接回我们大急诊
金莉从1月30日正式和同批其他9位护士、4位医生一起进入隔离病房工作,历时18天,于2月17日与第二批医护人员交接后撤出。
17日至今,他们一直在区里为医院抗疫征用的酒店房间中自我隔离,到本月底才能“重获自由”。
“现在每天除了领饭,就只能在房间里自己呆着,头一两天还好,后面就……”在酒店房间里跟记者视频通话的金莉笑起来很好看,让人想起时下流行的那首歌,“2003年SARS时,我就报了名想参加我们院支援地坛医院的医疗队,头发都剪了,结果后来不需要了,没去成。这次倒是赶上了,不过头发都没来得及剪就接病人了。”
在隔离病房里,每班6小时,需要提前1小时到岗,40分钟穿防护服,然后交接班。“挺锻炼人的,进去的,都成了‘小能手’——医护、清洁工、修理工、心理咨询师。”
金莉是家里的“顶梁柱”,但这一个月,家里的老母亲和10岁的女儿是指不上她了。“还行,她们都能理解,只要正确操作、防护到位就没什么问题。”

刘芳医生
和金莉同批进入隔离病房的原急诊急救科医师刘芳,1990年生人,今年刚好30岁。“非典的时候我还上初中呢,没想到这次亲历了。“刘芳报名参加隔离病房工作时“理直气壮”——“我单身,家里有姐姐照顾父母,没负担;我又是急诊专业,对紧急情况的认识和处理会比较及时;再说我还是党员。”
说起现在在酒店自我隔离的感受,刘芳说,“太憋得慌了,之前在隔离病房值班的时候,好歹上下班还能在外边走走,夜里2点去上班,下个雪,还能在路边踩踩……病房里虽然有风险,但我知道只要我正确操作,就是安全的。其实在病房里心特别静,不用考虑任何其他的复杂问题,只想着你的病人就好了。”
视频里的刘芳掰着手指头算了一下:“下周一我们应该就能出去了,我不打算回家,直接回我们大急诊去。”据说,医院急诊在疫情中的压力和风险一直很大,“急诊是不能拒收病人的,但各种各样潜在的传染可能性一直存在,比如有的病人可能本来发烧,但吃了退烧药后,又因为其他不适症状来到急诊……”

尽医生的本分,心里最踏实
从1月25日到2月25日整整一个月,副院长郝宇红只在2月22日至23日这个周末没到医院。23日晚,医院又收治了后来引发广泛关注的湖北女子监狱刑满释放、带病回京的黄某。
郝宇红在普仁医院此番成立的新冠肺炎防控工作小组中任副组长、医疗救治小组负责人。
2月25日下午1:30至2:30之间,她在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个小时中,每隔几分钟就要接打电话或被急匆匆找她处理问题的医护人员打断。
13:45,接电话,讨论一会儿要转过来的疑似病人如何安排;
14:00,再次接听电话安排两例疑似病人转诊事宜;
14:16,与焦急前来找她的同事讨论病历上有关流行病学史的内容、病人常住地址与暂住地址的不同填写方法;
14:25,接电话讨论一例“边缘患者”(咽拭子阴性、有慢阻肺、胸片显示肺部严重炎症但不像新冠肺炎的患者)的安排——无法确诊、不敢收在普通病房,又一时无法按重症肺炎转院到有条件抢救的医院……
14:28,院领导找来催办一例治愈病人的出院手续及捐献血浆知情书事宜……
忙碌的间隙,郝宇红说起隔离病房启用初期的紧迫。“为了降低防护风险,我们规定医护人员进入隔离病房不能带手机。而隔离病房中的固定电话又不能满足内外医护人员沟通、会诊病情的要求。隔离病房紧急启用,一时不好解决这个问题的情况下,我跑到家附近的营业厅办了一个手机卡,用我自己的IPAD注册了一个名叫‘隔离病房’的微信号,让首批进入病房的医护人员把IPAD带进去,最初的病例会诊、内外沟通就是用微信视频电话完成的。”
后来隔离病房内外沟通用上了“小鱼易连“”腾讯会议“等软件。专为此次疫情成立的院医疗专家组6位核心专家,一开始是在门诊楼放射科读片室与隔离病房进行网络视频会诊,之后才将会议室改造成远程视频会诊的专用空间,专家组成员也扩大到了12位。
再忙再乱,郝宇红也还是清晰地记得收治的第一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她50岁,1月30日转到我这儿,2月22日才出院。其实她算新冠肺炎普通型,入院三天就退烧了,但就是核酸检测总是反复。通常病人体温正常三天后,连做两次核酸检测(隔日)均为阴性,就可以出院隔离观察了,但这位患者每次做这样的检测时,总是第一次阴性、第二次阳性(或可疑),就这样反复做了七轮检测,才终于全部呈阴性,允许出院观察。”
2003年非典期间,30岁出头的郝宇红还是普仁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17年前那条件比现在差远了,当时人已经进到隔离病房了,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呢,后来眼看着通道被木板封住、来给我们送饭的人在门口搁下饭就跑开,才觉得不对劲儿,家里人打电话进来,眼泪一下就哗哗的。”
“现在无论是医疗条件,还是防控流程,都规范了很多。就这样,也是真累……要比较的话,说实话我还是宁愿像非典那时候一样进病房,当医生的,尽本分的时候心里是最踏实的。”
文/本报记者 张楠 供图/北京普仁医院
责任编辑: